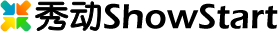“记忆经过许多个中介,以朱丽叶·比诺什或红白蓝编织袋的形式出现,将我个人的疼痛翻译成我的语言。只有这一件事是真实的。”
——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疼痛部》
疼痛是唯一真实的证人,被疾病和法兹音墙搞坏了脑子的年轻人们总是拿脑袋死命往南墙上撞,不头破血流就死不悔改,头破血流了也照样。语言也被撞的四分五裂,失去了依靠的叙事只能被血液和泪水填满。再也没有的意思就是再也不会有了,我们只剩下满脑袋脓包证明大家曾经尝试过做点什么,最終回の再放送は音箱无休止的回授啸叫与耳膜没完没了的疼,最后一次的重放是(?
第一次出门远行前血液里沸腾的无力与痛感无数次提醒我们应该尽早告别这种你死我活的吵闹音乐,但是不行,再怎么疼也改不了。我们真的像兔子一样享受被猎人等待的感觉,因为反正也没地方可跑了。疼痛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做好准备,法兹效果器拧到头捅进音箱已经过载的电子管,拿着麦克风随时准备给自己的一脑袋包火上浇油,21世纪已然被法兹效果器扭曲了心灵的弗兰克辛纳屈在用泪水猛击调音表时不停地大喊大叫:“有些东西永远打败不了!语言也变得无力了!”然后我们不再说话,在大家面前用力撕开自己直到血肉模糊,当众揭开自己的伤疤总归是件羞耻的事儿,但是谁让我只会这个呢。
于是河南疾病孩子们春暖花开(并没有)之际出门巡回,冬天结束的时候总得有点什么动静,最終回の再放送必须得没完没了。想到自己在厕所哭着边踹马桶边写出来的那些东西要唱给这么多人听,真是像梦一样奇怪的长途旅行。Chara唱:「いなくなった私を消し去って,この腕の痛みさえも,いつか私を捨てていく だから」(我不懂日语这是复制粘贴的),不知道一路上我们能抹杀自己几次,脑袋和手腕内侧还是生疼,那就这样吧,希望曲终人散的时候大家都能好起来。
乐队介绍

五个河南孩子的十七岁黄金合唱团。
嘉宾介绍

The Beneficial Society
The Beneficial Society 是一支来自杭州的screamo/post-hardcore/emo乐队,用直线摇滚乐嘶吼出情绪之声。

反复攻击小明
世界上已经存在着么多好听的音乐了,我们为什么还在努力创作?简直是自取其辱!